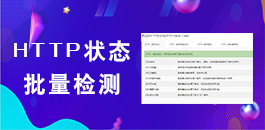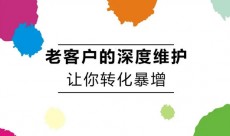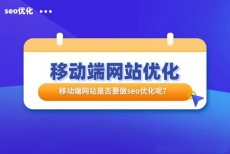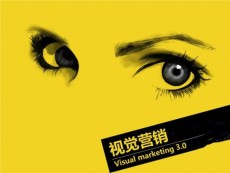- 歡迎使用超級蜘蛛池(CJZZC)網站外鏈優化,收藏快捷鍵 CTRL + D
一个新媒体牛马自述,中年危机“满35减10”
25 歲就被“優化”的新媒體編輯,用 4 年從 10W+ 作者變成無業游民:行業萎縮、AI 搶活、一人多崗、工資腰斬。當 35 歲危機提前 10 年殺到,在一線城市做內容,連垃圾袋都缺的日子,成了他們最真實的注腳。

一、入場
和大部分互聯網人的經典開局一樣,我入行的原因也是招聘信息上的“專業不限”——那時的新媒體正值風口浪尖,無人在意你的學歷背景。
那時的微信公眾號如日中天,公司的幾個賬號都是日更,幾乎每篇都是真實數據10W+。
我的工作是原創文字內容,配上畫面腳本,然后交給插畫師繪制畫面,做出的文章叫做“條漫”,賬號的類型叫條漫號。
經過幾個月的適應,我從一開始的每天都想離職,到每個月績效第一,終于站穩了腳,開始期待升職加薪當領導。

加薪是加了,因為當時有明確制度,一年兩次的調薪我每次都拿到最高額度。至于升職,我似乎是排了半天隊,輪到自己時碰巧售罄的那批。
原本部門的人員結構是編輯-副主編-主編-總監,22年開始逐漸撤銷了副主編和總監,主編沒有向上晉升的空間,自然也騰不出空給編輯。
我對此其實沒有太大意見,因為大部分打工人只在乎能拿到多少錢、干得累不累。工資比同事高,還不用像主編一樣整天開會、見領導、協調工作,倒也自在。
于是我把唯一的重心放在內容上,剛工作時能力達不到,只想著快點出稿完成KPI,穩定下來之后想寫出好的內容,讓讀者和自己都滿意。
我做出了一些成績,成為領導和同事眼里最可靠的那個,但時間沒有放過新媒體。
互聯網行業的人員流動性很大,身邊的同事換了一撥又一撥。或許是預測到公眾號的沒落,比我資歷老的兩個編輯很早就轉崗,后來離職去其他公司了。

最夸張的時候全組編輯只剩我一個是老人,其他幾個都入職不到半年。感覺自己像固定刷新在工位上的NPC,每個新人都向我請教經驗,有一種《重生之我在新手村練到滿級成為大魔王》的感覺。
后疫情時代的23年,公眾號部門已經從頻繁換人變成了持續減員,編輯和插畫都在經歷一場不可預知的狼人殺,我旁邊的工位在送走一位00后女生之后再也沒有迎來下一位嘉賓。
到了年底,部門原本的三個組合并成兩個組,我負責兩個賬號的內容,升級成了懷舊服新手村大魔王plus。
彼時部門的人員配置已經精簡到幾乎裁無可裁,留下來的都是共事了幾年的老同事。
和剛開始裁員時的“微焦慮”不同,大家逐漸佛系,因為除非老板不做公眾號了,否則也就維持這樣了。
公眾號的數據的確在三年內快速下滑,但廣告客戶的數量和單價下滑要慢得多,這或許就是上學時書上說的市場經濟的滯后性。
扣除我們的工資成本,公眾號仍然能給老板帶來正收益,這也是為什么大家都不覺得老板會在短時間內放棄它。
但正如電視劇里皇上最忌諱被人揣測出心意,如果你我牛馬能預測老板的想法,那我們就不是給人打工的了。
二、離場
把時間線拉回21-22年,老板對短視頻發起探索,陸續從公眾號部門抽調了一些人手組建抖音和小紅書團隊。
一年后我發現了一個規律:轉去做抖音的同事有著共同且唯一的結局——離職。
內部抽調已然無法滿足日益擴張的規模,大量博主、攝影師、運營等入職了公司,那時抖音團隊的位置就在公眾號部門前面。
公司的前半部分每天鑼鼓喧天,討論熱烈,博主換著妝造跑來跑去,攝影和運營對著屏幕手舞足蹈;而在后半部分,一群人坐在電腦后面安靜但興趣盎然地注視著一切。
和當年的公眾號不同,22-23年的短視頻賽道已經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前方的抖音項目組平均三個月換一批人,每次新人來的時候,上一個博主不要的衣服化妝品還堆在工位周圍。
彼時全國的MCN公司如雨后春筍,相比之下做大做強的頭部賬號屈指可數。人員頻繁流動實屬正常,畢竟這就是互聯網,這就是新媒體。

隨著公司重心的轉移,抖音和小紅書部門日漸龐大,也能看到有不少商單。
但據我所知并沒有體量太大的賬號,也沒有出圈的爆款,至少和當年的公眾號比,他們沒有我們火。
或許這是作為公眾號一方的我嘴硬,但這最后的倔強也不是沒有依據,畢竟除了裁員,這兩年公司在其他方面也在堅持節流,想必是在開源上不太順利。
有一個關于互聯網公司的古早梗:看一個公司好不好就看公司的紙巾。
我入職時抽紙堆在公司茶水間隨便拿,兩年后改為到前臺領取,一次一包。當然,沒有離譜到一些網友分享的那種需要登記的程度。
我不太理解的部分是關于紙巾的好兄弟:垃圾袋。
即便在還沒找到工作的今天,我也從未讓家里的垃圾桶著過涼。你可能很難想象一個幾百平米的辦公室,垃圾袋長期短缺,讓公司保潔阿姨都感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記得當時我跟同事打趣道:如果將來哪天公司上市了,一定是歸功于少買垃圾袋節省下來的錢。
至于下午茶零食和生日會等縮水,影響同樣不大。而年終獎,我在職不到4年,總共只拿過一次。
第一年我在試用期,沒有年終獎,公司開了年會,抽獎抽到一支口紅,和女同事換了個藍牙音箱。年后開工紅包100。
第二年拿了年終獎,不到一個月工資。括弧,當然是年后才發的,括弧完。公司開了年會,抽到安慰獎紅包一個,內含10元。年后開工紅包10元。
第三年沒開年會,沒有年終獎,年后開工紅包5元。
第四年沒開年會,沒有年終獎,年后開工紅包5元。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和同事們最后的叛逆是把五元鈔票粘在工位隔板上長期展示。
不過其中某一年(具體是23還是24年記不清了),準確來說其實并不是沒發年終獎,而是公眾號部門沒發年終獎,有些部門是發了的。
至于我為什么會知道,因為發這個年終獎的時間是上班時間,地點是公司會議室。會議室里人聲鼎沸,充滿了快活的氛圍。
人類的悲歡各不相通,坐在20米外工位的我們只覺得吵鬧。這一幕的藝術成分,大概有三四層樓那么高。
即便已經離職一年,我仍未想通這樣做的目的。私下發不讓我們知道,也就不會有什么不平衡。如此高調難道只為羞辱一番我們這些“舊時代的殘黨”。

時間線回到24年5月的某個下午,我們被通知“公司業務調整”。公眾號部門將不復存在,組內人員幾乎一個不留。
我們最后這批人,此前見慣了公司的人員優化效率,因此也并沒有太大反應,輪流前去光速簽字,帶著N+1當天離職走人。
唯一不理解的部分,就是前面說的,沒想到老板真的會徹底不做還有營收能力的公眾號了。
收拾物品和格式化電腦時我沒有做任何拍攝記錄。有這個意識是因為新媒體人的職業病,沒有做是因為彼時的“離職博主”自媒體賽道同樣人滿為患。
當年的一曲藍蓮花,配上“青春沒有售價,硬座直達拉薩”的文案,催生了大量互聯網離職博主,只是如今大部分或許都回北上廣深上班了。
三、嘗試返場
離職的當天晚上我有過短暫的焦慮,但看到銀行卡的余額,這種焦慮很快煙消云散。
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我第一次見到這么多錢。
此前我沒有存錢的習慣,因此除了每個月發工資的那天,這是我的銀行卡里第一次出現五位數。
離職的第一個月,我和同事們聚會了幾次,互相又把這幾年公司的八卦翻了個底朝天。
之后的兩個月,忙著幫女朋友搬家,把她之前租的房子退租,搬到我租的房子,然后換家具、重新裝飾一番。
秋天我們去外地玩了兩次、參加朋友的婚禮、看了一堆電視劇和電影、花了大量時間在各自的愛好上、每天研究晚飯做什么。
人一旦上癮就很難停下,我對這樣的“退休生活”上癮了。
有時會在一筆大額開銷后猛地打開掌上銀行看一眼余額,想著明天不點奶茶了,然后光速原諒自己。
其實在很多個節點,我都想著要去找工作了,但上有對策下有對策,仿佛左腦攻擊右腦一般,我總能找到相應的理由拖延下去。又或者是工作的這幾年經歷了太多DDL,現在終于開始了對DDL遲來的叛逆。
7月的時候,作為一名資深球迷,我說等歐洲杯踢完就找工作。
9月10月在外面玩,我說等深圳天涼快了就找工作。
12月天涼快了,我說年底沒有好工作,年后再找吧。

值得一提的是,不上班的日子并非一無是處,離職大半年后,我的“工作病”痊愈了。
互聯網一項廣為流傳的共識是:不上班之后身體和氣色會變好、脾氣也會變好,有一種肖申克從陰暗下水道爬出來重見廣闊天地的美好。
大概是畢業工作的半年后,我開始出現不定期的頭痛,每次持續幾天。如果要對其程度做一個描述,大概是老三國里的曹操、甄環轉里的宜修,或者胡軍版朱元璋里的朱標。
在百度看病和布洛芬治病無果后,我前后去了三次醫院,看了三個科室(急診、神經科、內科),收獲了新媒體版三顧茅廬的傳奇經歷。
三個科室給出的診斷分別是偏頭痛、三叉神經痛、叢集性頭痛、情緒性頭痛。(其中某個科室給出了兩種可能)
幾種不同的藥物沒能起到效果,我不再糾結自己到底得的是哪一種頭痛,畢竟理論上大部分頭痛和口腔潰瘍一樣,屬于“無法有效治療”的“絕癥”。
而我無法忘記的是給出情緒性頭痛診斷的那位主任醫師,問診時給我把了脈,搭上我手腕大概五秒左右,他便問我是不是工作壓力比較大,總是費腦思考;那一刻我對中醫的敬畏程度達到了頂峰。
后來每年我都會犯病幾次,每次也沒別的,就是硬抗。直到去年冬天,我發現自己再也沒犯過頭痛。“離職”先生真乃神醫也。
年后春暖花開,告急的銀行卡余額讓我和女朋友不得不真的著手準備找工作。
用春暖花開也許并不恰當,因為2024年的深圳根本就沒冷過(廣東的冬季一般是12-2月,其他時間是夏季)。
作為一個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的人,我第一次遇到整年沒有冷過的情況,最低溫度的那幾天也不過短袖外面加件外套。
所以24年冬天的極端氣候一度讓我懷疑世界末日要到了,直到年后找工作我才恍然大悟:是新媒體寒冬把冷空氣都吸走了。
當我做好簡歷打開招聘軟件,瀏覽一番之后得出了結論:新媒體的崗位,質量斷崖下滑。
首先是我的老本行編輯崗,微信公眾號的衰落和AI的發展取消了大部分崗位,很多公司不再需要運營公眾號,或者使用AI生成的文案簡單應付,我此前堅持的所謂有質量有靈魂的原創內容,似乎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棄子。
放寬到短視頻和其他新媒體方向,招聘軟件上的崗位大概有以下共同點:
1.一個崗位同時負責微信微博抖音小紅書快手頭條知乎等所有平臺。
2.一個崗位同時要求文案寫作、攝影、圖片后期、視頻剪輯、做PPT、做excel、公文發言稿寫作、采訪、發展客戶等各種能力。
3.需要在接近0成本的情況下從0到1做賬號,要求粉絲和流量增長,產品銷量增加。
4.薪資待遇水分嚴重,互聯網教會了用人單位把工資拆解成幾部分,一看標題一萬五,實際到手七八千。
四、復盤
放在相親市場上,這叫許愿;放在就業市場上,這個就叫新媒體。
35歲失業的程序員已經是上個時代的互聯網難民,如今25歲的新媒體人想找一份新工作,要么工資腰斬,要么一人分飾多角。
大部分公司更愿意頻繁更換價格低廉、吃苦耐勞的大學生,而不是有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挑三揀四不好應付的成熟新媒體人。
“高中地理課本上的‘優勢是廉價勞動力’,多年后發現竟是自己,年少的子彈如今正中眉心。”這句話近兩年很火,不知是誰第一個反應過來這一點,但一邊狠狠共情,一邊把它傳遍網絡的,一定又是新媒體人。
2025年的新媒體工作者,尤其是微信行業,像極了超市晚上關門前的生鮮柜臺,疊滿了buff。
一邊是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資源:公司多、行業發達、熱度高;一邊是求職和招聘之間的溝壑:工資談不攏、工作內容談不攏、績效KPI談不攏、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晚上打折的肉其實早上剛屠宰,但如果不降價賣掉只能進回收站垃圾桶。25歲的新媒體人也不老,但不大幅降低要求的話,或許真的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以前只覺得晚上在錢大媽提前一個小時搶好東西等著一小時后結賬的人群不可思議,現在我也想去試試了。